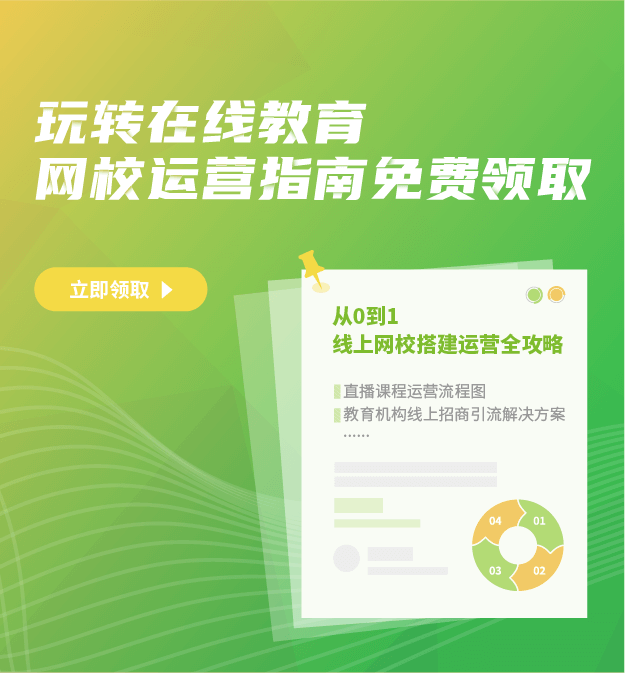过去,主流教育者们会毫不迟疑地认为,远程教育是一种内容贫乏、毫无人情味的教育形式。然而,北美、澳大利亚、亚洲和欧洲的传统大学都采用了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这些学校大概认为自己能把远程教育搞得更好,至于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不得而知,因为根本就没有MOOC这种实体,而且其定义还在迅速增加。仅就名字来理解MOOC的概念更是一种误导。总之,MOOC要比以前的在线教育形式更简单、更缺人情味:没有教师,没有指导,没有学费,也没有入学要求;学生唯一需要的设备就是购买电脑。成千上万的学生学习同一门课程;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和评阅作业。教材是电子形式的,由新兴的出版MOOC资源的行业提供,利润可观。有些MOOC还鼓励学生之间而不是和教师建立沟通网络。此外,根据MOOC为世界各国迅速接受来判断,它是迄今为止最易于实施的教育形式。
典型的MOOC运营模式是教育机构和提供多媒体MOOC资源的外部供应商签订外包合约。2012年2月,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创建了Udacity。截至2013年4月,Udacity提供了24门课程,仅注册前两节视频课的学生就达9万。截至2013年6月,Coursera已与70所高校签约合作,包括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MOOC的另一平台edX于2012年5月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联合成立,但主要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教授领衔运营。edX首先开放了七门课程,其中一门课程的注册生数达5.3万(Classroom in the cloud,2012);截至2013年6月,edX的合作机构达28家。媒体和博客对MOOC的报道迅速增多。在本文撰写前的六个星期里(2013年3月中旬),谷歌快讯(Google Alerts)找出400多条与MOOC相关的最新信息,其中有些是关于MOOC的消极信息,使用了诸如灾难、不幸、混乱、惨败、暴民统治以及MOOC蜜月期等词汇。到2013年5月中旬,当时本文正在校对中,关于MOOC的激烈争论把MOOC的两个诞生地——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职人员迅速分为两派,争论话题包括MOOC的商业化会使大学教师失去对课程内容知识产权的担忧。也有学者对MOOC的优缺点进行了全面评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等知名人士对MOOC给予乐观支持(Friedman,2013)。2013年初的众多评论对MOOC的未来充满期待,这些评论成了MOOC运营商的营销新闻,以及那些计划推出MOOC课程的大学的宣传预告。总之,自始至终都能听到“哇喔”的欢呼声——博茨曼用来评论随新技术而生的、不加批判的宣传用语的常用感叹词。
然而,MOOC并不是全新的事物,如何实施也有众多经验。远程教育机构有20多年的在线教学经验,也了解不同教学法的优势和不足。例如,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合作学习可以促进学生间的相互指导,但也会给人际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因此需要有精心的教学设计和指导。针对各种媒介的教学设计原则也有100年历史。巴格利曾推荐高效教学的16条原则(Bagley,1911),其中的15条被保留在楚(Chu)和施兰姆(Schramm)1967年出版的教育电视节目设计指南中(Chu & Schramm,1967)。2003年,在斯各特(Scott)等人提出的“通用教学设计”(universal instructional design,UID)原则中,这份教学原则清单被缩到九条(Scott et al.,2003)。上述三份教学原则清单涵盖九条显而易见的指导原则,如要求教学设计明确一致;教师有灵活性;能包容学生错误,强调师生互动的重要性。尽管通用教学设计原则不再强调教师必须为学生提供反馈信息和知识,也不强调自主学习的重要性,以及适应教学文化差异的需要——自称“通用”的教学设计原则忽略以上三条真是奇怪!2013年的清单也没有强调早先提出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合作学习,或许是因为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MOOC的欢呼者当然希望学生明白他们的期望。他们的网站(如https://www.edx.org)展现了学生的张张笑脸,就像老早宣传画中幸福的耕耘者一样。然而,MOOC似乎没有遵循近百年来受信奉的任何一条教育原则。师生互动和反馈早已过时,合作学习虽有问题却大受欢迎。显然,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客.管理人员不需要鼓励就会抛却陈旧的教育原则,摆脱教学法、教室乃至教师而将学习的责任明确放在学生身上。罗伯逊(Robertson)在其《不再有教师,不再有课本》著作中对这一趋势表示哀叹(Robertson,1998)。诺布尔(Noble)批判远程教育数字学位工厂的崛起,声称其运作完全受商业利益的驱使(Noble,2002)。笔者注意到,两位作者甚至在自己任职的远程教育机构公然谴责MOOC,认为对其违心认同简直就是异端邪说。这或许是好事,因为许多远程教育教师已经开创了细心周到的教学法,即便是通过远程教育方式也能给学生提供美好的教育体验,但其他教师未必如此。作为一个整体,远程教育实践者或许已经意识到,远程教育易遭人诟病,但他们仍迟疑不决,不愿因为承认某些合理的批评而扰乱整个系统。
但是,罗伯逊和诺布尔都准确预见了MOOC时代的来临。诺布尔描述了科罗拉多大学和瑞尔教育公司于1997年签订的合约。该合约规定,科罗拉多大学必须要求教师设计在线课程材料,大学拥有材料的所有权(Noble,D.,2002)。诺布尔指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也签订了类似合约。诺布尔惊讶地发现,几乎没几个教师因为意识到此举给自身可能带来丧失知识产权的风险而出来反对。当时,人们很容易无视诺布尔的担忧,认为其耸人听闻。毫无疑问,诺布尔用夸张的语言描述了MOOC的发展——“就像本能一样,人们排好了队,‘没有一点差错’”,“(而)管理者却坚持发展有利可图、与行业有关的学科,孤立或淘汰拒绝追随的少数派”。2007年,瑞尔教育公司更名为eCollege公司,被全球最大教育出版商皮尔森(Pearson)公司收购(Wikipedia,2013b)。2012年,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成为第一所为完成MOOC课程的学生授予学分的大学(Mangan,2012);而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特瑞萨·沙利文(Teresa Sullivan)因为校董们认为她在追随MOOC带来牟利机会方面做得不快而几乎失去职位(Daniel,2012;DeSantis,2012b)。由此看来,诺布尔的警告也不是那么耸人听闻。
多头的海德拉怪兽
MOOC诞生并得以发展的传播媒介,即所谓的博客,凭借迅捷的发布速度加速了MOOC的推广和应用。博客空间里自称理论家、哲学家的新生代们赋予其“MOOC”的名号并宣告MOOC的来临。命名行为或许也对其推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出现的是全新而重要的观点。事实上,没有多少教育原则的大规模交流模式取代了传统的扎实的教育原则(Bates,2012;Hartman,2013)。加拿大博主西蒙斯(Siemens)和唐斯(Downes)创造的流行语“联通主义”吸引了人们对班杜拉(Bandura,A.,1977)、布鲁纳(Bruner,1961)、维果茨基(Vygotsky,2012)等教学论设计前辈,以及帕斯克(Pask,1975)等网络技术特定领域专家所提出的原则的关注。
MOOC的早期拥护者也许并未预见,他们创造的这个古怪的概念会被政治和商业利用,在大规模在线发布和传播中获利。西蒙斯(Siemens,2012)曾使自己远离各种形式的MOOC概念,认为应当区分xMOOCs和cMOOCs:前者仅仅是“知识复制”,后者则由“联通”的学习者生成知识。同时,MOOC概念的各种变体不断涌现,就像多头的海德拉怪兽(Hydras)。海德拉是希腊神话中剧毒的九头蛇,传说只要砍断其中一颗头,立刻又会生出两颗来(Leadbetter,1997);而MOOC的拥护者对批判作出的回应就是不断创造新的名称,如MOODLE(Holton,2012)、MOOC版(EduSoho,2013)、UniMOOC(UniMOOC-Tec,n.d.),以及身份不明的“微MOOC”(Bartoletti,2012)和“迷你MOOC”(Glader,2013)。最后两个变体显得特别牵强,多少显示出对MOOC批判的担忧,似乎想要通过先发制人的方式表明他们的MOOC真的很小。维利(Wiley,2012)是“规模不大但开放”课程的评论者,他的评论催化了MOOC概念的生成(Wiley,2007)。他举例说这一首字母缩写词会使人误入歧途,它唯一准确的一点是,所有MOOC都在线,就像绝大多数现代远程教育课程一样。
有些MOOC规模宏大但不开放;有些MOOC开放但规模不大;有些MOOC尽可能不以课程的形式呈现;“我讨厌这一概念”,维利写道(Wiley,2012),“那些‘规模宏大但不开放’的MOOC课程对开放教育资源的未来发展是一种威胁,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警示人们,MOOC热潮和追随者制造出的混沌概念将快速蔓延,会瞬间失去控制。
早期关于MOOC的评价毁誉参半。菲尼等(Finietal.,2008)回顾了2007年维利在犹他大学的课程。他们认为,该课程有较好的教学法,并合理运用了开放教育资源,它“将是大学真正的机遇。以这种方式大学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开设课程……,它为专业发展课程和终身学习的实施提供了现实样板”。菲尼也分析了学生对2008年9月至11月间西蒙斯和唐斯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开设的“联通主义与联通的知识”(CCK08)课程的反应。他报告了学生每天吸收信息的积极反应,以及他们对各种耗时的社交媒体与质量良莠不齐的在线视频的看法。迈克涅斯等人(Macknessetal.,2010)评论说,CCK08课程的目标是实现学生的“自治”。学生对该课程大加赞赏,可是他们发现需要课程指导时,自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觉得有指导会更有帮助,”一学生写道,“自由很重要,但这门课的内容却很零乱,没有一处空间可以就某个主题对最新思考进行持续探讨”。迈克涅斯等人的报告显示,仅14%的参与者完成了该课程。他们指出,学生被论坛中的大量信息“淹没”,仅“导论”论坛就有1000多帖子,由学习该课程2200多人中的560人发布。迈克涅斯等还描述了学生对“恶劣行为”和“高人一等的说教性跟贴和举动”作出评论。他们最后评论说,“虽然技术促进了联通,却不能保证互动”。类似情况在后续课程CCK11也有(LaBonte,2012)。总之,鼓励学生运用社交媒体相互联结,从理论上看似乎是有效的,但是没有为学生推荐联结的路径或许使这一任务变得困难重重。
尽管2007和2008年犹他和曼尼托巴大学的课程已经从大学服务器上撤走,读者仍可以通过访问web.archive.org来评判这些课程以及曼尼托巴2011年课程的价值(Siemens&Downes,2008,2011;Wiley,2007):课程结构、用法说明以及资源和学生个人信息被保存在一起(如姓名、电子邮箱、论坛的帖子等)。这一切证明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实践,也违背了1997年曼尼托巴政府发布的《信息自由与隐私维护法案》。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转折期,为MOOC的实践提供了警示。2003年,中国大学作出把课程外包给外部供应商,也就是“网络学院”的决定(Chen et al.,2010)。到2005年,成立了6000多个校外学习中心,半数以上由69所远程教育机构独立经营。陈和王对533名城乡师生进行调查后公布了上述做法的效果。教师们抱怨和网络学院缺乏联系,无法委派和监督教学指导者。在这些网络学院中,70%“从未进行过任何远程教育研究,而且……管理者丝毫没有意识到研究的重要性。其余30%声称做过一些研究,但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尽管某些网络学院根据ISO 9000标准设立了内部质量保证机制,但只有20%的机构为教师提供了培训;迄今为止,中国在线教育的质量一直时好时坏,难以界定。
这些问题对在线教师而言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已经研究了十来年学生对在线教育的评价。《在线与远程学习国际研究述评》涵盖了60项由我的学生对在线学习方法利弊的评价。我对学生提出的警示记忆犹新(Carter,2009):
教育者和决策者面临着资源减少而基础设施成本增加的困扰,数据被随意地“塞进”沟通渠道而沟通本身却没有得到相应改善。特别是在大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技术被最大化地使用而人员之间的直接交流被无限缩小。孤独和心理距离不断拉大。
创立三大MOOC平台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们是否了解和关心这些警示呢?霍尔顿(Holton,2012)说: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没有一家MOOC运营商雇用任何接受过教学设计、学习科学、教育技术、课程设计培训的人员,或者其它教学专家来帮助实现他们的课程设计,雇用了一大批程序员和教师,抱着各种目的参与这场开放教育实验。edX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六千万美元支持,的确值得称道,却只雇了一个人负责课程开发。”
万维网服务经理科米尔也在评论中提到教学设计的缺失。在描述理想的cMOOC时,科米尔(Cormier,2010)认为,系统设计的忽视或许是有意的:
“课程是分散的,所有的博客、讨论、视频、文章、信息和标签……通常不是集中出现,而是覆盖整个网络,出现在不同的空间和群中。学习没有正确的途径,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单一的路径……,只有你可以判断自己最后是否成功完成了课程。”
本·约翰逊效应
唐斯(Downes,2012)曾经讽刺自己帮助创立的MOOC的发展进程:“一旦(MOOC模式)获得成功,它会立即被常春藤联盟采用(常春藤联盟会因这一“发现”而赢得称颂)。对这一点我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这是我们这一领域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也一直影响着加拿大人。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开始,无数加拿大新闻人物吸引了全球眼球,却很少有人过问他们的原籍(McLuhan,1964)。当然,偶尔也会出现负面情况,而此时,加拿大人会迅速否认自己的国家成就——比如,1988年奥运会上,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赢得100米短跑金牌,这毫无疑问是加拿大人的荣耀。整个加拿大迅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CBC/Radio-Canada,1988)。但其后由于约翰逊被认为服用兴奋剂而剥夺金牌时,加拿大媒体仿佛瞬间想起他是牙买加裔(CBC/Radio-Canada,2012)。未来几年内,首先推动MOOC的加拿大人会悲伤地彼此提醒,他们当初极力倡导的想法已日渐远去。或者他们应该感谢最初的荣耀已渐行渐远,因为尽管唐斯(Downes,2012)表示MOOC模式已证明成功,但最后的结论显然还有待分晓。
未来,MOOC可能会被视为教育救世主而广受追捧,或者成为教育发展篇章中难堪的一页。一旦大众的追捧遇到阻力,MOOC最后落得颜面尽失,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学院会将责任归咎于给予MOOC这一缩写词的那些人吗?反之,如果MOOC的设计和传播问题得到解决,MOOC取得胜利,是否还有人会因为别的原因指责早期的MOOC追捧者——比如说,拆了传统远程教育机构的台,毁了远程教育市场?因为到那时,公众面临的问题是在阿萨巴斯卡大学和凤凰城大学,或者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提供的MOOC之间作选择。回答这些问题应该不需要太久,开放式博客媒体的好处就是使用者能对新方法给予即时反馈,不论优点还是缺点,就像前面提到的学生评价一样。
MOOC的演变
在MOOC的发展中,主要运营商Coursera、edX和Udacity始终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大规模的学生让教师无法管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MOOC通常采取简单的方案——让学生相互教学和评判。结果2013年初,一些资深元老们开始发言,对这一举措表示忧虑。罗米斯佐夫斯基(Romiszowski,2013)指出,MOOC绝不是什么新事物;贝茨则质疑,为什么像麻省理工学院这类机构会推崇MOOC,却无视(之前在线教育)25年来关于有效教学设计的经验与研究(Bates,2013)?纳伊杜(Naidu)指出,MOOC的价值在于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教育实践,它的成功取决于它们能否有效应对教—学面临的共同挑战,如学习者投入、大样本评价和反馈。我记得,教育技术的元老们以前从未同时公开发表过如此意见一致的评论。
2013年6月,托尼·贝茨和另一位远程教育专家约翰·丹尼尔爵士与edX主席阿纳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专题讨论上交换了意见。丹尼尔强调,MOOC运动无视开放课程4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Daniel,2013)。2013年7月,阿加瓦尔接受美国深夜脱口秀节目“科尔伯特报告”的采访(Comedy Central,2013)。尽管贝茨、丹尼尔及其他人一直在唱反调,阿加瓦尔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再次重申自MOOC提出以来就极力称颂的准则:学生联结、学习者导向、摒弃教师的价值。但是,技能娴熟、问题尖锐的主持人史提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对阿加瓦尔“大规模、开放、学习者即教学者”等观点表示怀疑,听众们的哄笑显然证明,他们对科尔伯特的讽刺极为认同。听众和主持人站在一边,形势对阿加瓦尔明显不利;面对科尔伯特的警示,阿加瓦尔本可以为自己做更好的辩护。不管怎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线学习受到大众电台的嘲讽。刺耳的笑声表明,MOOC并未受到美国社会的认真对待,跟我们阅读学术期刊和博客后所认为的截然不同。采访提醒我们,这些天花乱坠的炒作如何欺骗了我们,让我们相信如果不追随潮流就会落后于时代。事实上,或许卷入潮流的才是少数派。
对于这一结论,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根据最新的《地平线报告》,MOOC已有一席之地,只需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为主流教育所接受(Johnson et al.,2013)。但《地平线报告》的预言也曾失误(Baggaley,2013a);百森调查研究小组(Babson Survey Research Group)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教育机构支持MOOC的比例实际上非常低(Allen & Seaman,2013)。大多数美国高等教育机构(55.4%)对MOOC持观望态度,其中32.7%没有推出MOOC计划。仅2.6%的机构声称目前正在尝试MOOC;计划推出MOOC的大学比例稍高,为9.4%。这与《地平线报告》认定的“主流应用率”应达到20%的数字相去甚远(Johnson et al.,2013)。
经历数月的多事之秋,重要时刻终于在2013年9月到来。哈佛大学——MOOC最有前途的赢家之一,竟然摒弃两条重要原则:大规模和开放性。哈佛大学教学中心主任、在线试运营课程主席罗伯特·卢埃(Robert Lue)教授声称,哈佛大学现处于“后MOOC时期”,将提供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简称SPOC)课程(Coughlan,2013)。字母M(大规模)和O(开放)似乎如我们所见,正从浪潮中消逝。哈佛大学的SPOC是指限于几十到几百人的“小型”课程,而且参与者的筛选是“非公开的”,要经过封闭的申请流程——换句话说,这就是远程教育机构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供的在线课程!谁能想到常规的远程教育方法会如此迅速地在主流教育中找到位置?!
其中的解释当然是,哈佛大学用SPOC缩写来暗示在线教育最新版本的新颖之处,正如大规模在线课程运营商用MOOC缩写来凸显他们的创新一样。如果说2012-2013年人们对MOOC一词的把玩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传统大学在批判多年后开始支持在线教育,从而挽回了面子——这是丹尼尔列出的有关MOOC趋势的众多悖论之一(Daniel,2012)。这一趋势的另一副产品就是促使教育视频的再度流行——一种值得欢迎的回归。现在网络宽带足以让视频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同时保证良好的传输效果,就像MOOC一样,虽然目前质量还良莠不齐(Winter,2013)。
MOOC安魂曲?
即便是在大规模课程中使用视频也不新鲜,阿匹库尔(Apikul)提醒到,巴基斯坦虚拟大学(VUP)为1万名学生提供同步的在线和卫星电视课程已有10年(Apikul,2013);中国和印度的开放大学类似经历也有30年(Baggaley and Belawati,2010)。因此,现在说MOOC过时还为时尚早,巴基斯坦虚拟大学提供的设计成熟的课程既能保证宏大的规模和开放性,又能遵循教学指导原则(Malik,2010)。当然,要是MOOC一词已开始变味,那么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就可能不再叫MOOC;而且从出现的对MOOC的评价来看,MOOC供应商(Coursera,2013)认为他们的课程适用全球,这一点毫无根据(Liyanagunawardena et al.,2013)。这些评价包括:缺少发展中国家参与者对MOOC的评价,许多学生在体验MOOC联通主义和学习者建构的学习方法时仍存在很多问题(Baggaley,2013c)。
当前,人们对MOOC大规模和开放性的质疑,对宣扬MOOC理念的人来说不算胜利,尤其对西蒙斯(Siemens,2008-12)和唐斯(Downes,2008-13)来说不算——西蒙斯甚至已经与MOOC保持距离(Siemens,2012,2013)。由他们团队提出、用来证明学习者中心理念重要性的所谓“联通主义”理论(Downes,2004-12;Siemens,2005-12)也受到质疑。他们对之前详细阐述相同观点的学者给予了很少甚至零的肯定,而且评价也认为西蒙斯和唐斯设计并管理的早期“联通主义MOOC”存在教学法缺陷(Baggaley,2012,2013b)。克拉拉(Clara)和巴贝拉(Barbera)也批判联通主义没有创新性(Clara,M & Barbera,2013),责怪其出现太快而没有时间让学习者在网上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讨论。网上讨论尽管无法达到传统的学术标准,但可以获得即时评论(Lange,2011-2013)。朗(Lang)甚至指责联通主义是毫无根据的骗局。朗的批判过于激愤和尖锐,以至于联通主义支持者们谴责她过于强调精英主义,并且因为情绪激动是否具有可信度(Mackness,2011)。然而,从哈佛大学摒弃MOOC原则和联通主义来看,我们很难忽视朗的评论。人们甚至可以以她的评论预测MOOC的起落。
MOOC是新技术迅速得到采用的典型代表,印证了加特纳的“技术发展周期模型”(the Gartner Hype model)(Daniel,2013)。目前,MOOC的发展处于该模型的“期待高峰期”,未来数月它们能否会加入教育云计算和虚拟世界,将在“期待低谷期”揭晓。我时不时在想,我是否应该将传统发表方式与博客相结合,在这个能作出即时评论和反馈的令人兴奋的世界里为自己搭建一个平台。不过,MOOC的演变同样没有在博客世界里取得胜利。
博客就像会议报告,提供的是初始平台,来检验那些没经过传统出版物审查的观点。它们把各种热心人士聚集在一起,捍卫他们未经检验却认为新颖的观点,而当这些未经检验的观点用大胆的缩写词或以“ism”结尾的行话包装后就显得特别可信。一项针对“博客空间”的分析显示,博客总能吸引志趣相投而排斥意见相左者,所以他们的观点可以毫无阻碍地迅猛发展(Adamic & Glance,2005)。MOOC2008年以来在博客空间的发展就是例子。受商业利益驱使,并让人们明白MOOC是全新的观念,有人创造了MOOC这一可爱的缩写词;而他们的游说也引发了博客空间关于“学习者即教学者”的讨论风暴,这种不堪一击的观点在严谨的学术出版物中绝对不会出现。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MOOC现象宣扬了“教师无足轻重”的观点。从这一方面而言,这场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以各种媒介形式承载的不良教学的关注。否则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必须在严肃的学术讨论中为教师的一般价值辩护这一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